无常年代里的生命请愿
- 2022年3月18日
- 讀畢需時 4 分鐘
已更新:2022年3月21日
“零年代”(2000~2009年)转瞬间已经过去大半,转型时期充分显露出它的“测不准”特征。几乎所有的媒体都热衷于在年关预言未来,但世事却总是飞奔在预言者的前面,粉碎那些无知的预言,迫使其呈现出某种荒谬可笑的嘴脸。
2005年元宵节前,香港坊间盛传一个著名预言家发出的警告,称九龙地区当晚将有重大事件发生,闹得人心惶惶,结果一夜过去,一切风平浪静。又一个惊心动魄的预言崩溃了。但这也许不是预言家的过错,而是基于时代“不确定”的古怪特性。它神秘莫测和变化无端,导致了先知的挫败。发生在2005年的印度洋海啸,来去无踪,诡异而又险恶,屠杀了将近60万无辜的生灵,但此前却没有任何一个预言家发出过警报。预言的无效性,就此转述出我们存在的格局。

西安大雁塔寺的青年香客(朱大可摄):神交易的风气,在佛教和基督教里大量发生
世事难料的境况,导致了契约型宗教的普遍发生。这种宗教是以贿赂神明为本质的。信徒在偶像前虔诚祝祷说,请神保佑我达成这样那样的目标。神的使命一旦完成,信徒将兑现他的贿赂――出资修缮庙宇、或者再塑偶像的金身。人神交易的风气,在佛教和基督教里大量发生,但它已经不是真正的宗教,而是一种镶嵌在宗教里的祈祷经济,它要用货币的魅力引诱神,以期在神的帮助下握住自身的命运。
大规模的贿赂运动,正在成为中国文化中最蛊惑人心的部分。我们无权苛责这种求助模式,因为它完全符合市场的教义。我时常在那些著名的寺庙里徘徊。越过香火缭绕的寺院和大殿,可以看见那些虔诚的香客。神在他们的背影上书写无字之书,但没有人能够阅读其中的真意。寺庙的话语是用晨钟、暮鼓、松涛、木鱼和诵经声编织起来的,这些元素汇成了人神交易的柔和背景。香炉里积淀着大量香灰,这是膜拜的礼具,也是信徒灵魂的灰烬。它们在风中舞蹈和吹散,暗示着信仰本身的不可靠性。
盘旋在宗教场所里的动乱气息是令人不安的,但民众抗拒命运无常的最激烈方式,并不是寺庙朝拜,而是在传统节日里燃放烟花爆竹。后者基于某种奇怪的信念:巨大的声响和耀眼的焰火可以惊醒沉睡的众神,促使他们起身观看民众的痛苦,并为世人的财富和幸福提供保证。燃放烟火,就是要借助火药发出惊天动地的请愿。
民众的这种自救运动,无异于对神的精神迫害。我们可以想象众神(财神、菩萨、观音、土地公等等)为此所承受的巨大痛苦。他们被震耳欲聋的声音暴力所驱动,成为所有燃放者的家奴。但这种声音巫术最终要支配的却不是神祗,而是人自身的命运。烟火神学的伟大意义就是如此。

春节放鞭炮仪式:这是要借助火药向众神发出惊天动地的请愿
世事的无常性,是中国人长期探讨的核心命题。早在动荡迷乱的魏晋时代,有关无常的哲学已经深入人心,那就是用潇洒的立场去维系朝不保夕的生命。隐逸、佯狂、逃亡,在一个战战兢兢、如临深渊、如履深渊的语境里,自由生命随时可能走到尽头。蔡邕隐逸在朝廷里,为董卓起草文告,实践着文人们所盛赞的“大隐”策略,却仍然无法摆脱被王允诛杀的命运。
据《世说新语》记载,阮籍驾着马车肆意游玩,到了道路的尽头,放声大哭,伤心而返。那么,阮籍为何穷途而泣?在道路的尽头,他究竟看见了什么?他是否洞见了自己的未来?没有任何典籍能够回答这些疑问。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,这个人的痛苦,来自于他的形而上困境。他哭泣,正是基于他的走投无路。
这是典型的魏晋困境,也是中国人的历史性难题。行走就是一次对道路的书写,它向人打开了未来的诸多可能性。但突如其来的判决打断了这种可能性。阮籍的哭泣是一次自我悲悼,因为他在道穷之处看见了最高的“无常性”――甚至寻常的道路都拒绝对他开放。他被囚禁于一个存在的迷津。
处理生命无常性的策略,在魏晋这样的转型年代里流传开去,甚至曹操这样的国王都发出了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”的慨叹。流传在战争年代的《何日君再来》,向世人劝诫说:“好花不常开,好景不常在。愁堆解笑眉,泪洒相思带。今宵离别后,何日君再来?喝完了这杯,请进点小菜。人生难得几回醉,不欢更何待?”这是古老的“及时行乐”策略的近代翻版,它以流行歌曲的方式指引了20世纪的中国民众。著名的歌手邓丽君本人,因这首歌而走红,最终却以她自己的猝死,验证了躲藏在歌辞里的谶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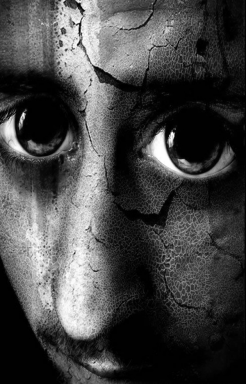
安德森《死孩之脸》:她以她自己的猝死,验证了躲藏在歌辞里的谶语
死亡的普遍发生,将是历史学家用以描述“零年代”特征的主要方面。这里不仅包含陈逸飞式的突发性病故,还包括各种大规模矿难、毒气泄漏和险恶的车祸。而最不可思议的是,除了先秦和文革,中国人还没有任何时候像今天那样视死如归。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提供的数据宣称,中国每年至少有25万人自杀,200万人自杀未遂。自杀者的庞大队伍遮蔽了种族的视野。那些广场上的自焚者点亮了衣衫褴褛的肉体,逼迫我们凝视自己的命运。
大部分自杀导源于社会公正之不确定性。它是人的最后和最粗暴的抗争,企图终结毫无指望的生命,并籍此探寻失踪已久的正义。死亡的烈焰照亮了茫茫黑夜,也照亮了隐匿在黑暗里的事物。面对普遍的罪恶和不公正,自杀者义无反顾地站立在那里,对生命的不确定性作最后的反叛,而后迅速化为尘土。死亡就这样喊出了对秩序的渴望。
(原载《记忆的红皮书》,花城出版社,2008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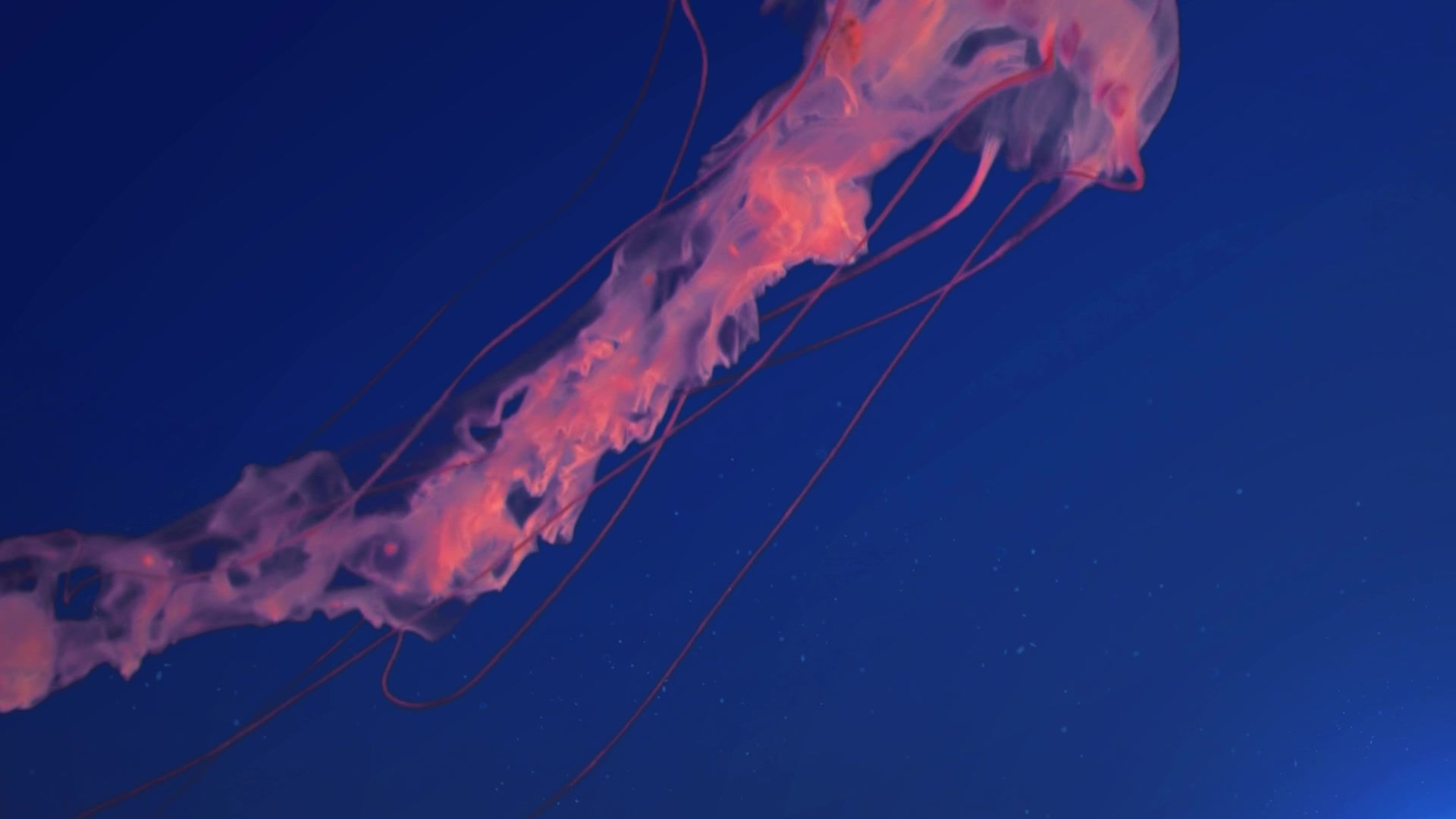






Commen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