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细读旅美女作家周励女士关于胡适先生和夏志清教授的回忆,对徐复观与李济在胡适之死的悲剧中所扮演的角色,尤其是张爱玲乖戾薄凉性格的细节,颇感震惊。这些个人叙述,于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,都有补偏救弊的重要意义。
以我的陋见,张爱玲的写作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。在第一时期,她接受港大熏陶之后,于1943-1944两年,在上海出版小说《沉香屑》等女性文学作品,就此名扬文坛。在第二时期,她在上海推出红色主题小说《十八春》和《小艾》,那是她黑色旗袍上唯一的两朵红花。在第三时期,她1952年再赴香港,创作英文小说《秧歌》和《赤地之恋》并受到胡适的夸赞。在第四时期,为了对付生活所需,应宋淇之邀,她投入了电影剧本创作,如《人财两失》和《南北一家亲》之类,但那些脚本对她的文学书写毫无裨益。
到了第五时期,张爱玲三临香港后重返美国(1962),能量和才华都在迅速褪色。她的英文投稿被多次退回,《红楼梦魇》作为唯一的学术专著,写得枯燥乏味,毫无才情,成为其江郎才尽的明证。除了自传体《小团圆》尚有寡淡的早期余韵[ 参见唐娒嘉《张爱玲“小团圆”未刊始末及其晚期写作危机》,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,2024年第1期。],其他作品都善乏可陈。这一时期竟长达33年,劫走了张爱玲75年生涯的一半。
今天我要谈论的,恰恰是张爱玲的第五时期。她跟夏志清之间的各种关联,主要发生于这个阶段。此时,夏志清作为文学批评家正在走向成熟,并发现张爱玲第一时期作品的卓越价值。
但这种认知却诞生在张爱玲的四、五时期之交,也就是她开始走向衰退的年头,远远晚于她的黄金岁月,由此产生了某种显著的时间性错位。不仅如此,过去时态的张爱玲作品,跟现在时态的张爱玲人格,两者之间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调。这种罕见的双重错位,给批评家和张粉们带来了严重的困扰。
但周励的《此情可待成追忆——与夏志清张爱玲有关的胡适等四君子之死》[ 原载微信公众号“留美学子”。](以下简称《此情》)所提出的问题,并不止于张爱玲的才能衰退,因为这是每个作家都须面对的困境。例如,鲁迅在北京、广州和上海的三个不同时期,就曾出现文学原创力的强烈落差,因而仅此一点,并不足以引发世人的惊愕。

问题的焦点恰恰在于张爱玲的人格状态。周励的文章,从道德审判入手,批评她是极端自恋自私和薄情寡义的女人,敌视整个世界,敌视隐瞒中风事实的丈夫赖雅,尤其敌视倾力助己的友人,不仅对恩人夏志清毫无情义可言,而且直接导致恩师陈世骧的猝死。这方面的细节零乱而真切,几乎充斥着整个第五时期。
夏志清对张爱玲有知遇之恩。张的第二次走红,盖缘于夏志清的英文著述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。后者逾越常规,盛赞《秧歌》乃“不朽之作”,《金锁记》是“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”,而张爱玲因这样的文学成就,就当之无愧地成了“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”。[ 夏志清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,2005]
这种毫无保留的溢美之词颇为罕见,却对张爱玲的“中兴”起了决定性作用。几乎被世人遗忘的张爱玲,从此梅开二度,以台湾为中心,重新散发出迷人的馨香。到了九十年代末期,张爱玲甚至成为中国小资青年的最高旗帜,飘扬于上海乃至整个内地的文学天空。
在《此情》里,周励回忆了她在20年前与夏志清夫妇关于张爱玲的对话。我们被告知,张爱玲在抵达美国之后,受到夏志清在事业上的父兄式照料。夏毕生仅见过张四到五次,却因赏识其卓越的才华,又顾惜其落魄的现状,将她力荐给赖氏女子学院翻译《海上花列传》,又推荐她成为佛罗里达大学当住校作家,还把她推荐给台湾皇冠出版公司,为她争取到稳定的版税收入,如此等等,可以说帮到了不遗余力的地步。
但一个反向的事实是,夏氏夫妇除了收到过张爱玲的一百多封“求助信”[ 夏志清《张爱玲给我的信件》,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,2013。]以外,从未收到过她的任何礼物,包括签名书及照片合影,也没有收到过她的就餐邀请。她甚至拒绝向夏提供自己的电话号码,更很少拆看夏给自己的信件。耐人寻味的是,根据周励的回忆,夏生前对此竟毫无怨言,反衬出他的人格博大。

如果说张爱玲人格的势利凉薄,对于夏志清的伤害尚属有限,那么其恩师陈世骧因张而猝死,就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,显示这种“凉薄”已经到了“令人发指”的地步。陈世骧身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东方语文学系主任,因受到夏志清的鼓励,聘请张为该校中国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。这是张爱玲在美国最“辉煌”的两年。
张在受聘之前,曾寄赠过稀缺的木函装《梦影缘》及线装《歇浦潮》,以及自己作品《北地胭脂》等,但在赴任后就换了一副面孔,不仅拒按学校作息制度准时上班,也很少跟陈沟通,陈夫妇屡次邀她到家作客,都遭张的拒绝,[ 陈少聪《我与张爱玲擦肩而过》,中国时报人间副刊,2005.7.13] 更对其同事如杨牧和娜拉夫妇倨傲寡情,以至于双方关系紧张;因其研究论文迟迟不能达标,张又跟陈世骧发生多次激烈冲突,最终导致陈于盛怒之下将张解聘。[ 夏志清《张爱玲给我的信件》,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,2013] 一个月后,陈便因愤懑和抑郁而猝发心肌梗塞谢世。在周励的叙述中,张就是陈死亡的直接诱因。
周励还援引了另一个由张爱玲引发的猝死案例,主角是台湾诗人兼文学评论家唐文标。他是台海“张爱玲热”的另一重要推手。他拖着身患癌症的沉重病躯,耗费大量心力和资金,收集上海沦陷时期的零星图片、佚文、残稿、访谈、评价等,也即一些被张本人及公众遗忘的“历史碎屑”,然后以影印方式编成《张爱玲资料大全集》,由时报出版公司推出,“客观上记录了张爱玲文章的特色,为深入了解张爱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。”[ 纪忠璇、符爱萍《张爱玲小说的批评体系研究》,依大中文与教育学刊,2022.3]
周励认为,对于这种仅有学术价值而无市场价值的图书,张爱玲应该心存谢意,或以协商方式探讨版权问题,搭建正常的合作关系,而她竟把碎屑当做“沉香屑”,痛斥其侵犯版权,要求出版社立刻终止发行,而唐在搬运库存的四百册书回家时,因上楼梯时用力过度,引发鼻咽癌手术伤口破裂,次日凌晨在荣总医院不幸仙逝。[ 参见季季《唐文标的张爱玲》,转引自谢其章《“唉,唐文标,爱死了张爱玲!”》,澎湃新闻之上海书评,2018.2.7]

周励据此评价说,“与其说张爱玲是个孤傲清高的女人,还不如说她是个势利冷酷,圆滑机巧,‘有事有人’,无事无人(好友宋淇语)的‘心机女’。”这是一种措辞严厉的道德批评,而且由于夏志清对张爱玲来信的诸多注解,似乎已经成了难以辩驳的事实。
该文发表以后,引发了圈内人士的诸多反响。夏志清的弟子唐翼明说,周励“写张爱玲的凉薄、自私、势利,入骨三分,与我对张爱玲的推想一致。”而对于张爱玲的崇拜者而言,这种真相的揭示却是令人窒息的,它摧毁了文学社会反复营造的流行偶像。

道德祛魅,是针对大规模造魅运动的一种价值反转,它逼迫崇拜者以更理性的方式,去看待有人性弱点的社会名流。借助资讯时代的消息传播,人们已经发现了大量令人沮丧的事实。例如,在梅毒症的冗长名单里,赫然出现了莫扎特、舒伯特、贝多芬和舒曼的名字;在美术域则有梵高、高更和马奈;在文学域有福楼拜、莫泊桑和波特莱尔;在思想域有尼采和叔本华。[ 参见德博拉・海登《天才、狂人的梅毒之谜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] 托尔斯泰虽跟性病无关,但他的忏悔/救赎主义外衣下,却是反摩西诫律的生活真相,而跟他的小说叙事迥然相异。[ 参见《托尔斯泰最后的日记》,天津人民出版社,2020;以及:保罗·约翰逊《知识分子》第五章:托尔斯泰:上帝的兄弟,新华出版社,2005] 对张爱玲的道德重估,应该就是这种文学祛魅的最新动向。
但在我看来,仅仅使用道德指标来评判作家的言行,是远远不够的,反而极易造成某种溢出性伤害,因而有必要添加另一种重要的解读工具,那就是临床精神分析。此类工具在文学批评领域很少运用,是因为存在着文学和精神病学的专业壁垒。而在张爱玲的个案上,这种工具的运用尤为重要,否则,我们就无法对那些基本事实做出更深入而准确的判断。
我要追问的是,在张爱玲道德失调的背后,是否还存在着偏执型精神障碍(Paranoid Disorder)的因素呢?答案是显而易见的。
第五时期的张爱玲,始终坚信自己被跳蚤攻击,导致她浑身瘙痒,无法忍受。这种对虫子的妄想,正是偏执型精神障碍的典型症状。此外,我们还能通过大量书信和他人的口述回忆(包括张的好友宋淇和水晶),发现那些自恋(自卑)、孤僻、逃避、冷漠、猜疑、仇恨、受侮辱和迫害妄想等多种亚症候。

只要对照《默沙东诊疗手册》(Merck Manual of Diagnosis and Therapy)或《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》(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,DSM)[ 这两种手册的中英文版,都可通过互联网搜索引擎获得。] 提供的症状描述,人们就不难发现,她正是一名典型的精神病患者。该工具从另一个角度,揭示了张爱玲道德失调的病理根源。也就是说,那些被视为“有道德问题”的言行,可以(部分或全部地)追溯到她的精神病源。
根据张爱玲写给宋淇的信件可以获知,“恐虫事件”源于第五时期的1983年,当时公寓管理人通知住户配合出清橱柜,喷杀蟑螂,为此张被迫将物品移出室外。但在将物品重新放回屋内之后,她却意外发现了不速之客——跳蚤。[ 宋淇、邝美云《张爱玲往来书信集》,台湾皇冠文化,2020]
这是何其严重的入侵事件,自此,她以柔弱的肉身,拖着病入膏肓的灵魂,开始了漫长的逃亡历程。她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狂奔,反复变更居所,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。起初她每天更换一家汽车旅馆,而后则是旅馆和租房的彼此交替,就这样长达数年之久。而在她身后狂追不舍的,是跳蚤、虱子、蚂蚁、甲虫和蟑螂的幻象大军。
张爱玲对人诉说的跳蚤,尽管肉眼无法看见,却可以被她清晰地描述。比如1985年3月在致宋淇夫妇的书信里,张爱玲就认定骚扰她的跳蚤分为两类,第一类是从邻家猫狗传入的黑色跳蚤,第二类是搬家后随二手冰箱隔热层带来的浅棕色中南美品种。[ 同上。] 而医生诊断表明,所有这些“虫子叙事”都是幻觉,因为她患有“虫子妄想症”(Bug Delusion)或“过敏症”,后者是一种更为温和的诊断术语,用于削弱病人的抗拒情绪。
但这两种诊断都遭到张本人的否认。就像绝大多数精神病患者那样,她拒绝承认自己有病,而坚持将所有问题外推给跳蚤,令这种吸血性昆虫无端躺枪。这意味着她还患有比本源性精神病更为严重的继发性疾病——病感失认症(Anosognosia,一译“病觉缺失症”)。它之所以严重,是因为它产生了自我吞噬的怪圈,让疾病变得不可医治。
更耐人寻味的是,随着张爱玲的一路逃亡,跳蚤的身量居然逐渐变小,犹如细长的枯草屑,但直到1986年9月,这些跳蚤依旧还在纠缠不休,而且“每次快消灭了就缩小一次,终于小得几乎看不见,接近细菌”,[ 同上。] 因而完全无法被医生检出,更无法被他人看见。后者被称为“继发性妄想”(secondary delusion),是病人为解释其病态性经验──跳蚤骚扰的躯体妄想(somatic delusion)所产生的新一轮妄想。[ 参见吴佳璇《张爱玲的身心症与文学梦》,联合文学,2013.02.11] 她顽强地守望着自己营造的幻象,满怀恨意,夜以继日。
这种多重叠加的虫子迫害妄想,于1991年到1995年期间达到高潮。在这时期,心力交瘁的张爱玲暂停逃亡,选择在洛杉矶罗切斯特街10911号公寓206室定居。她在那里修改旧作《小团圆》,指望跟往昔岁月做一次小小的“团圆”。惊人的巧合在于,她猝死的1995年9月8日,恰好跟“中秋节”重合,以至于它像是一种刻意的设计:在这象征“团圆”的古老节日里,她不仅结束了跟胡兰成的“小团圆”,也实现了跟死神的“大团圆”。

根据我的现场观察,该陋室位于二楼长廊的尽头,距电梯口(坏人和跳蚤出没处)最远,却因紧挨消防楼梯,而距逃生通道和地面最近。显然,她选择了该建筑物中最为安全的方位。难以理喻的是,作为一个作家,她的屋里甚至没有一张用以安放文学和餐食的小桌。
毫无疑问,她很早就已为下一轮的轻装逃亡做好了准备。但在那间陋室里,她的爬虫妄想症再度发作。她死后身上一丝不挂,可能就是为了避开躲藏于衣物中的可恶跳蚤。但这次她放弃逃亡,转而以决绝的方式终止心跳,宣判自己跟虫子一起死亡。
年仅18岁的张爱玲,曾在散文《天才梦》[ 引自张爱玲《张看》,花城出版社,1997] 中写过一段名言:“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,爬满了虱子。”这其实就是一则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虫”的谶言。此语被张粉广泛引用,却无人揭示其中的深层语义。
这与其说在喻指自身的存在现状,不如说精准预言了虫子妄想症和作茧自缚的社交恐惧,还有对熟人圈的深刻敌意。在她眼里,夏志清和陈世骧,也许都只是“人形虫子”而已。最终,在生命之途的尽头,她卸下那袭“华美的袍”,告别虫子,裸身而退。这是张爱玲的悲哀,抑或也是那些赏识并帮助过她的友人们的悲哀。
所有这些病症,究其根源,应该都来自张爱玲的不幸童年。她的家族何其华丽光鲜,祖父为晚清名臣张佩纶,祖母为晚清重臣李鸿章之女,母亲是晚清南京提督之女,而家境却何其阴郁,充满不可思议的暗黑因素,令她陷入严重的失爱困境。这种黑白色调的强烈反差,勾勒出少女成长的悲剧调性。

首先是张严重缺乏来自母亲的爱抚和温暖。父母离异,母亲也在她三四岁时独自远走他乡,虽有短暂的复合,却又再度离去,直到她无法忍受父亲家暴出逃为止。但在她历经千险跟母亲“团圆”之后,却因后者的性情挑剔和管教严苛,依然无法得到长期渴望的关爱。[ 参见《童言无忌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,1994] 某次她得了伤寒,因为妨碍母亲跟男友出门旅行,母亲竟说:“其实你活着就是害人,像你这样只能让你自生自灭。”[ 《小团圆》,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2012年]
其次是严重缺乏父爱。张的父亲不仅吃喝嫖赌,而且是鸦片烟鬼,对儿女毫无怜惜之情,甚至施以暴力。一次跟继母发生冲突,张父不辨是非曲直,怒打女儿,还将其关进小黑屋达数月之久,她为此得了疟疾,差一点死掉,从中感到了“生如朝露,死如蝼蚁”的悲哀。[ 参见《小团圆》和《半生缘》(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2006年)]
不仅如此,张爱玲还合乎逻辑地饱受继母的冷遇。后者脾气暴躁、喜怒无常,对继女非但毫无爱心,反而视若贱婢。对于这位继母大人,张始终怀有厌恶之心,并为自己曾经被迫“捡她剩下的衣服穿”而感到无比羞耻。[ 引自《童言无忌》]
上述三位长辈组成闭环的三角形囚室,向张爱玲提供了童年的幽暗生态。它看起来如此恶劣,令她既缺母爱,又乏父情,加上长期在冰冷的寄宿学校(这类学校通常是疏隔和冷漠的象征)就读,毫无家庭温暖可言。这种孤苦的境遇,足以摧毁张的心灵,导致她自幼敏感多疑、自卑兼自负,严重缺乏安全感,并倾向于自闭和过度防卫。从她的回忆录《童言无忌》和自传体小说《小团圆》中,我们可以反复听见一个忧郁少女的病态性抱怨。

在此后的生命上升岁月,这些童年创伤一度得以平复,仿佛时光已经抹除一切,令所有的阴霾烟消云散,却在异乡的“逆境”中意外复活,再度放肆地发作,反复扩张,最终酿成灵魂的重症。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声称:“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,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。”张爱玲毕生都试图借助写作来治愈不幸的童年,却以彻底失败告终——她非但没有治愈童年,反被童年拖进了万丈深渊。
才华衰退、道德失调和精神分裂,其中的每一种危机,对于张爱玲而言都是致命的。而最为不幸的是,这三种怪物竟然互相缠绕和叠加,形成极其强烈的聚变效应。以张爱玲的孤傲个性、以及形单影只的异乡处境而言,她根本无力抵抗这三重危机的联合围剿,而她唯一的反抗方式,就是永无穷尽的逃亡。
张爱玲的经历向人们昭示,她毕生都逃亡的路上。前期从上海逃往香港诸地,后期从洛杉矶逃往洛杉矶。这逃亡可分为两个不同的层级——地理空间(物理性)和幻想空间(精神性)。就前者而言,她是巴金《家》里的男主角高觉新,通过出走而获得自由;但就后者而言,她更像是卡夫卡《地洞》里的鼹鼠,在黑暗地穴中打洞,营造复杂的迷宫结构,她要据此从三种隐匿、无名和强大的敌人那里逃开,却毫无胜算可言。
张爱玲的止步和谢世无疑是一种解脱,它迅速平息了灵与肉的全部苦痛。而对于这种决绝的断崖式解脱,我们还有什么可非议的呢?
谨以这篇文章,向怜香惜玉的夏志清先生致敬!

【说明】笔者曾于香港“夏志清、宋淇、张爱玲研究学术讲座”(2024.11)上,以《晚年张爱玲的三重危机》为题,作了七分多钟的视频发言。现对原发言稿加以修改和大幅扩写,最终形成这一更为完善的分析文本。2025年1月24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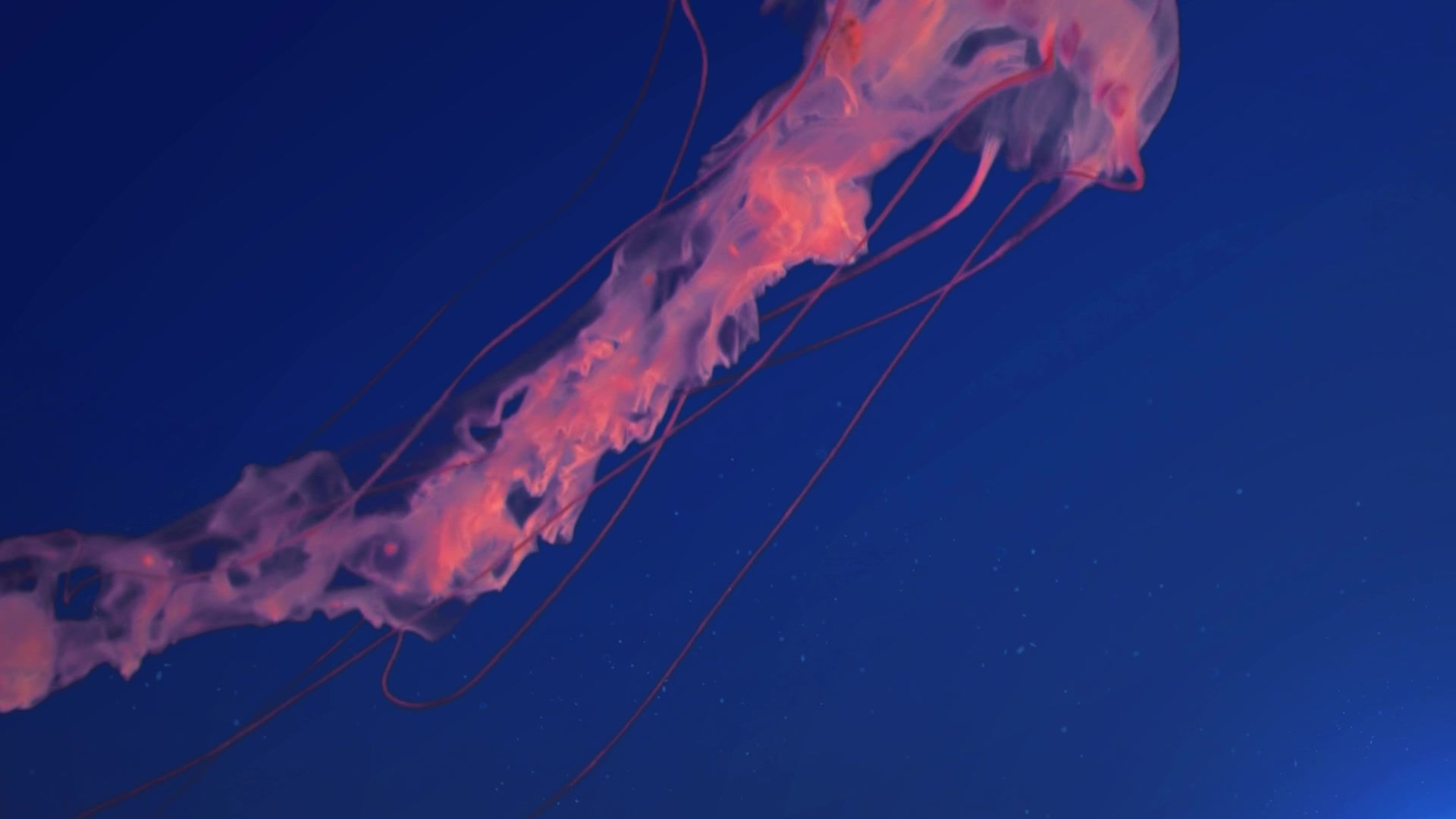



Commen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