祈福新村:第二代建筑乌托邦运动
- Deco Ju
- 2022年3月21日
- 讀畢需時 4 分鐘
中国南方是近代乌托邦的主要策源地。它制造了从“太平天国”到“三民主义”的各种乌托邦制度。我们至今还生活在它们的后果之中。1989年,正当中国北方陷入大规模动乱之际,一个新的建筑乌托邦在广州番禺开始策划和打造,这就是以后号称“中国第一村”的祈福新村。广东人以更加务实的立场,开启了新民居建筑的美妙历程。
以“新村”命名民居群落的传统,起自民国政府的三民主义构想。在当时的都城南京,诸如“梅园新村”之类的新式住宅已经开始林立。1951年,更为新型的“曹杨新村”在上海落成,则标志着斯大林模式的乌托邦民居的兴起。它们毫无例外地以“新村”命名,形成了20世纪的新意识形态建筑谱系。它们不仅维系着进城农民的村落主义记忆,也显示了城市无产者的天堂信念。
祈福新村是这个20世纪新村谱系的最后一环,却越出了毛式国家主义的构架。它既是旧日乌托邦的一个终结,也是新的资本乌托邦的开端。开发商耗资上百亿元,把266·7公顷农田变成了一座庞大的村落,拥有20000多户7万多人居住。而新的土地仍然在大面积开发。它正在迅速发育为所谓的“村落型精英卫星城市”。

祈福新村远眺
目前的祈福村民一半以上来自香港和35个国家和地区,其中包括一些裹着头巾的阿拉伯女人、黑人和欧洲白人。他们的存在构成了这座乌托邦村落的联合国面容。耐人寻味的是,其中大部分“富豪”是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偷渡香港的难民,他们在艰苦打工后储蓄了一笔钱,以“富人”的身份重返广州故地,指望在这个新式乌托邦里处理人生的晚期事务。他们用货币购买了自己的未来岁月。
被资本逻辑打造起来的居住乌托邦,拥有了乌托邦所必须的各种元素:富丽堂皇的俱乐部、庞大的泳池和餐厅、奢华的医院大楼、为有钱人修建的英语实验学校、保持中国传统种植业的度假农庄,被散步小径和路灯环绕的湖泊……,如此等等。每幢小楼前种植了芒果,居民每年都可以在一次统一的收割中得到30—50个芒果。这种意识形态水果曾经是毛泽东送给工人阶级的礼物,而如今却成为富有村民的幸福之果,悬挂在露台和前庭里,和龙眼树一起,照亮着每一座自我炫耀的庭院。
来这里周末度假的人们,喜欢在一个农家小院风格的餐馆里就餐,在闷热的夏夜里面对着夏天的一池荷叶,或者在会所里饮茶游泳,街上停满了宝马和奔驰。夜空上不时升起美丽的焰火,以节日的名义问候着这座非凡的村庄。人们还喜欢在湖边散步,遥望那些幸福家居的灯光倒影。它们在湖水里闪烁,放射着迷幻的光芒。这是乌托邦的的一种视觉属性,书写着所谓“祈福文化”的迷幻本质。

祈福湖的水光楼色
然而,这个90年代的富人乌托邦正在面对解体的危机。由于小高层的大批打造和平民的普遍侵入,别墅区里的“富人”们开始坐卧不宁。他们的天堂悄然变色,沦为平民的最新栖息地。广州的媒体在今年6月发出警报,声称已有80%的早期元老级住户从祈福新村撤离。呈现为铁门锈蚀、落叶满园、野草在院落里疯长的萧条景象。与此截然相反的是,祈福大道上充满着熙熙攘攘的平民人群。后者正在成为这个乌托邦的最新主人。
当你在新村大道上行走的时候,总是会被那些面容上所所洋溢的幸福表情所震惊。这种热烈的、充满私生活信念的气息,缠绕在村民的脸颊上,仿佛是一种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的历史再现。这其实就是祈福新村的真实表情,它像章鱼一样盘踞于广州城边缘,向南方的平民发出了热烈的召唤。

祈福新村甚至拥有自己的医院,一所高端民营医院
祈福乌托邦的这种阶层转型是一个典型案例:建筑资本放弃了对“富人”的呵护,转而亲近平民的钱袋,这一新的规划营销策略,以每平米3000元以下的价格,伤害了90年代“富人”的脆弱尊严,却最终完成了与平民、小资和新兴中产阶级的“接轨”。我们在祈福所看到的无非是平民的狂欢。他们占领了从超市、餐厅、穿梭巴士到广场的所有公共空间,并且在“富人”的地界上发出喜悦的喧嚣。4000名保安日夜巡逻放哨,捍卫着新世纪工薪居民的居住权力。
平民的大批入主,改变了这所乌托邦空间的性质,把它转换成了一个用低廉价格构筑的诗意栖居地。它不是一种政治赏赐,不是张扬意识形态成就的虚幻旗帜,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富人飞地,而是普通公民的坚实的生活乐园。这种戏剧性的改变,在北京和上海的房价飞涨(每平米一般都在5000~12000元以上)的恶劣情势中,显得尤为珍贵。让广大平民在可承受的价位上成为诗意家园的主人,这才是衡量地方官员政绩的基本标准。在我看来,祈福新村显示的不仅是开发商的资本战略转移,也向世人揭示了中国新世纪民居的基本方向。
原载《乌托邦》,东方出版社,2016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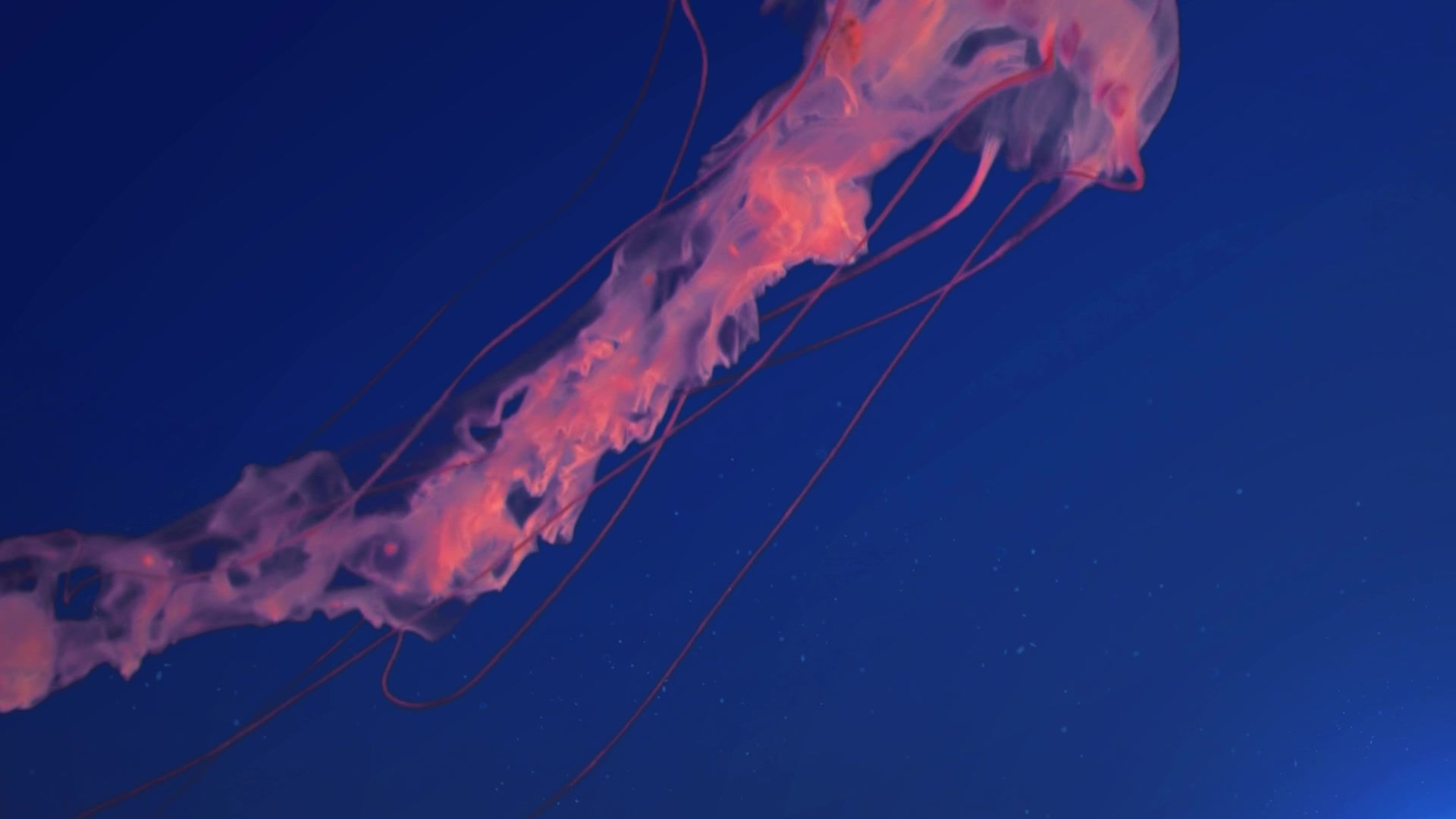



Comments